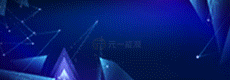2020年的起點上,在相當多的人總結過去的十年、展望未來的十年之后,所有人都受到了壓力、嘲弄、震撼甚至是震懾。這一切,都可以歸因于突然發(fā)生、并迅速蔓延的另一場非典型肺炎疫情——Covid-19。
盡管,作為流行病疫情,它會過去,或早或晚;它會變得不再那么可怕,社會成本或大或小。在它最終要成為歷史的那一天,我想我們會收獲很多的經(jīng)驗與教訓。更為重要的是,我們會更加敬畏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人文,珍視賴以生活的社會分工合作,珍惜賴以存在的彼此依靠。
從武漢封城開始,我們經(jīng)歷了噩夢般的五個星期,仿佛煎熬了5個月,甚至5年。而與此同時,悄悄到來的3月中旬,也是我國電力體制改革5周年的日子。這5年卻有一瞬的感覺。
過去5年,筆者在《能源》雜志陸續(xù)發(fā)表了《電力體制改革的成功標準與動力——基于9號文的討論》(2015年)、《電力體制改革兩年回顧:好的、壞的與討厭的》(2017年)和《電力體制改革需重新聚焦體制》(2019年)。
5年,我國電力部門的變化不大的說辭對持續(xù)努力中的同事可能有失公平。但客觀上,筆者必須強調(diào)電網(wǎng)管理體制、行業(yè)與企業(yè)文化、電價機制手段與水平比較等方面的“社會認識水位”有很大的提升,對于建設怎么樣一個不同的電力系統(tǒng)與部門,有了更多的“公約數(shù)”。在局部領域,比如輸配分開、售電等領域有些零星的新的進展。
但是就起作用的體制機制而言,也的確沒有什么變化是不可逆,與之前存在截然不同的范式。我國的電力行業(yè)仍舊是個理論上成本為基礎,實際上安全為目標,成本要求存在巨大彈性,也并不存在強管制的計劃經(jīng)濟部門。
在這樣一個5年的心理節(jié)點上,筆者對電力體制改革的難度的思考之后,也產(chǎn)生了眾多的敬畏,類似于對于病毒的破壞力與影響的敬畏。電力體制改革,是一項偉大的事業(yè)。它的難度,要大大的高于肺炎的緩解與治理。
本期專欄,筆者對電力治理與病毒應對將進行各個維度特點的比較,回答為何電力體制改革更難的問題。這種比較,主要從改革推進以及應對疫情的“政策推動”與“需求拉動”兩個視角來展開。
電力安全事故的反應時間遠遠短于病毒
電力系統(tǒng)與病毒防疫都面臨著風險(概率)與不確定性問題。理論上,緊急=概率*損失*反應時間/(避免失控的)干預時間,也就是說一個事情的緊急程度與概率、反應時間等幾個變量相關。
就新型肺炎而言,其概率很大,一旦發(fā)現(xiàn)可以很快干預(比如就地隔離)。相比于反應的速度,它考驗整個社會經(jīng)濟系統(tǒng)的韌性、資源厚度以及充分性。
而電力部門是需要隨時保持平衡的部門,任何的電壓頻率偏離標準值超過一定范圍,都會造成從電器損壞到大停電等一系列問題。這個系統(tǒng)發(fā)生事故在失控之前,往往留給人們的反應時間與干預處理時間都非常的短,比如幾秒內(nèi)就可能系統(tǒng)持續(xù)震蕩從而造成連續(xù)性的停電事故的擴大。從而,這個系統(tǒng)的安全保障一直像一根繃緊的“神經(jīng)”。
任何大的改變與變化,決策者必須衡量其潛在的技術風險以及由此產(chǎn)生的一系列經(jīng)濟、社會甚至是政治后果。改革的動力與意志不可避免的,將弱于病毒的防控。
“層層攤派”適用于病毒,但是對電力不適用
前蘇聯(lián)國家往往先有理論、然后再有實踐,我國則往往先有實踐,或者說“摸著石頭過河”。一個有效的計劃體制(比如蘇聯(lián))跟一個無效的計劃體制(比如印度)之間的差別,往往要大于一個計劃體制跟市場體制之間的差別。我們電力行業(yè)的計劃體制的有效程度,也介于蘇聯(lián)與印度之間。
“層層攤派”是計劃經(jīng)濟實現(xiàn)某個集體目標的法寶,盡管在很多時候,它很沒有效率,無法考慮搭便車與激勵等約束,也違反基本的專業(yè)化與法制原則,往往只能處理總量問題,而沒法子處理結構性問題。但是必須承認,它的有效性大部分時候是沒有問題的。對于病毒的治理就是這樣,我們看到了很多的“層層攤派”做法,非常之有效。
比如我們看到,應對疫情過程中,我們反復聽到“壓緊壓實屬地責任”,人民日報稱要“明確具體責任,一級帶一級去干,一環(huán)扣一環(huán)去抓,切實把各項防控工作逐一落到實處”。這是一種典型的“層層攤派”的治理方式。
電力部門恰恰是一個無法層層攤派的部門,它的范圍經(jīng)濟特別顯著,甚至是唯一選擇。
典型的,我國有5級調(diào)度,最高級的國家調(diào)度中心屬于“沒有責任,只有權力”的特權機構,負責割裂統(tǒng)一市場的特權線路的潮流計劃設定;省級調(diào)度是一個需要為系統(tǒng)平衡負責的實體,它卻不能把它的責任進一步攤派給下一級市級與縣級調(diào)度。因為電力的平衡,往往是越大越可行,因為可以有效平衡出力特性與需求特性不同的電源與用戶。
幾個地區(qū)的共同的最大負荷,一定小于每一個最大負荷的加總(也就是說,最大負荷出現(xiàn)的時間是不同的)。你無法把電力系統(tǒng)平衡責任攤派到每個市縣,每個工廠或者每個電廠,說“壓實責任,你自己平衡吧”。這無疑是荒謬的。
正因為這個特點,電力部門很多政策的討論,如果暗含著“層層攤派”的政策工具與實現(xiàn)方式,而缺乏有效的其他政策工具,就會徹底淪為空談。電力部門的問題往往需要更加的專業(yè)化,而不是采用整體性的方式去解決問題。這也是我國的電力現(xiàn)貨改革試點為何無法在“有效性”上推進的一大原因。
省級政府領了任務,無法像“煤改電”、“污染治理”、禁止散煤燃燒等總量問題一樣,分解到各個市去要求實現(xiàn)。短期市場解決的是成本最小化生產(chǎn)的基本效率問題。如果你把其他額外的約束加給它,那么這個市場就完全失去功能,成為一個玩具了;也因為嚴重的價格扭曲,不可能發(fā)育的起來。
病毒的對付手段是“隔離”,但是電力體制改革無法在真空展開
病毒,無論多厲害,我們都有終極武器——隔離以及俱焚,比如對付恐怖的埃博拉。這種方法短期是有效的,它意味著經(jīng)濟活動的損失甚至停滯,但是長期上往往是有益的。因為最開始,沒有人可以打保票說應對的措施過于寬松或者過于嚴格了。嚴格往往是風險管理的應然甚至唯一選項。
但是電力體制改革,無法隔離開國民經(jīng)濟以及與其他部門的互動展開,而這種互動,很可能產(chǎn)生意想不到,甚至是決定改革生死的結果。決策者至今也沒有發(fā)出過“寧愿冒著斷電的風險,也要堅決推動電力市場化改革”的決心信號。
2002年電力體制改革之所以夭折,無疑也是這個原因——衍生影響。2005年東北電力市場試運行,恰逢電煤開始漲價,抬高了上網(wǎng)電價,但銷售電價仍舊沿襲著相對固定的模式,傳導不出去,中間出現(xiàn)虧空。東北電網(wǎng)北部發(fā)電高價上網(wǎng),南部用電低價銷售的情況,以致東北電網(wǎng)公司16天虧損了32億人民幣。
按理說,這完全是煤價上漲的影響,跟市場改革完全無關,在煤價下降或者(應該)價格傳導之后還能夠有效的補回來。但是現(xiàn)實的問題是,建立一個資金蓄水池誰來首先出錢無法落實,從而造成了繼續(xù)改革的困難。
病毒治理外在對象,而電力體制要觸動人的利益
病毒作為敵人,是明確的,外部的。而電力體制改革,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最大的人造系統(tǒng)的自我革命,革命的途徑是體制與機制,盡管有可能做大蛋糕,但是存在“帕累托改進”(所有的人都受益,無人受損)的機會與體制基礎設施幾乎不存在,必然要觸動部分人的利益,甚至是很大的利益。即使存在通過轉移支付使得所有人都受益的理論可能性,但是現(xiàn)實中轉移支付的政治可行性往往也很低。
東北電力市場的試運行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?;ヂ?lián)電網(wǎng)的存在,理論上會做大蛋糕,但是無疑電力輸出省份要抬高電價而成為受損者,而轉移支付又存在操作性與技術性困難。黑龍江省和吉林省電力過剩,輸往遼寧,認為遼寧省有責任多漲電價,黑龍江省和吉林省不漲或少漲一點。而遼寧省并不同意,認為依靠本省市場消納其他兩省多余電力,不應承擔更多責任。這造成了改革最終散伙。
電價手段改革,取消交叉補貼也是一例。5%的人群,屬于社會弱勢群體,是公共政策與社會幫扶需要聚焦的對象,對其補貼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。但是這個補貼從哪里來,是個不得而知的問題,從而還得扭曲價格,讓95%的不需要補貼的人來搭5%的“便車”。
人們對病毒有切膚之痛,對要精算的高電價沒有
過去很長一段時間,我國電力部門采用的是成本為基礎的煤電標桿電價機制,以及保證的小時數(shù)。電價波動非常有限。默認的建成了就給足夠小時數(shù)回收投資的做法已經(jīng)形成慣性與習慣,對部分所謂專業(yè)化調(diào)峰機組也一樣,往往也給3000小時甚至更高,從而有效的降低了高電價投資回收的必要性,使得高的生產(chǎn)側電價不再(必要)出現(xiàn),天然氣機組(管制)價格也就比煤電高兩倍,甚至更少。這部分減少的小時數(shù)通過全體其他機組分攤,使得其長期平均成本上升。
全年統(tǒng)計來看,這種電價安排(比如365天4毛的電價),其總的系統(tǒng)成本,往往要高于一個360天低電價(比如3毛5),但是夏季用電高峰有那么120個小時高電價(比如1.2元)的系統(tǒng)。
從消費端,價格上漲的風險也被完全限制了,電價幾乎整年甚至幾年都沒有變化。這是一種“朝三暮四”的安排,但是筆者也很難否認這在政治上往往是屢試不爽的。人們可能更加在意那120小時令人咋舌的1.2元的高電價,而不是365天每天被擼0.5元羊毛的“溫水煮青蛙”。事實上,后者的全年總負擔要比前者更重。
比如在美國德州夏季用電高峰時期我國部分媒體非常吸睛的報道——《每度電63元!美國德州電價高出中國幾十倍》。事實上,全年來看,德州的平均批發(fā)電力價格也就不到4美分/度,比我國大部分省份的煤電標桿電價(需要扣除稅比較)要低的多。這種故意的信息誤導,我國消費者協(xié)會應該有個是否涉嫌欺詐的說法。
所以,公眾對電價是沒有切膚之痛的,但是對于病毒,那種真實與想象中的恐懼是現(xiàn)實存在的。因此,消費者作為利益相關方的壓力與推動是不同的。
理解病毒比想象中容易,理解電力部門比想象中難
網(wǎng)上很多的短片給人們充分講解了防疫的知識,以及快速積累起來的治療經(jīng)驗。人人都有意愿有望變成半個病毒治理的專家,理解其傳染的路徑、途徑、傳染力與病理影響。病毒會變異,但是趨勢是越來越弱。但是在電力部門,可再生進入電力系統(tǒng)完全是個全新的挑戰(zhàn)。
這一點對我國尤其是成立的。傳統(tǒng)上,我國的調(diào)度體系需要每一個機組都完全接受調(diào)度的指揮,所謂“接受調(diào)度指令”,可調(diào)可控。盡管這完全是一種沒有必要、過度與無理的要求,但是它的確是很有效的?,F(xiàn)實中也缺乏強有力的反對力量,促進“系統(tǒng)如何實現(xiàn)平衡”的范式的改變,因為運行了幾十年也并沒有太大變化。而可再生能源,是一個從技術性質(zhì)上就無法完全可控的發(fā)電類型。調(diào)度體系最初采用非常保守的“切除”來實現(xiàn)安全目標,造成了巨量的限電棄風。隨著可再生比例越來越高(特別是變化更加迅速的光伏),這種系統(tǒng)平衡的范式已經(jīng)越來越難以為繼。
從這個視角,可再生能源并網(wǎng),對于我國仍舊處于計劃體制的電力部門,特別是電力調(diào)度范式,是個“從地獄來的問題”。這一點,因為其專業(yè)性,還很難為社會公眾、甚至是部分業(yè)內(nèi)人士所理解。
治理病毒效果好壞比電力系統(tǒng)好壞更加容易衡量
當有一天疫情最終過去,對于治理病毒的集體行動是好是壞,是否足夠有效與有效率,我相信整個社會都會有一個評估。這種評估包括對過去采取的行動與方針的回顧,回答一個“當時的高度混亂與不確定的情況下,我們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處理這種情況”的假設問題;以及包括對從這起疫情的總結分析吸取教訓,會引發(fā)何種的未來的管理體制、應急機制以及人員組織調(diào)配上的改變。這兩方面,都是現(xiàn)代治理體系的基本內(nèi)容。
這方面的社會要求將是明確的。相比而言,電力部門的好壞以及改革的成功與否,似乎更加不可衡量或者爭議巨大。比如,對于我國占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(yè)電力行業(yè)領導人,其在意的事情往往是兩個,第一個是安全;第二個是個人晉升。第一個往往是第二個的前提與必要條件,但是遠遠不夠充分,并且標準存在模糊性,以至于現(xiàn)實中這些企業(yè)的行為中,相當部分“耍雜技”的成分存在,為了社會能見度。
比如《甘肅風電光伏電站集群開發(fā) 新能源并網(wǎng)瓶頸即將破解》一文稱:甘肅酒泉風電基地創(chuàng)造了距離負荷中心最遠、集中并網(wǎng)規(guī)模最大、送出電壓等級最高等一系列風電發(fā)展記錄。這是典型的“耍雜技”行為而無法證明其經(jīng)濟與社會理性。
一個高效的,充分開放競爭與嚴格監(jiān)管的電力部門與體制,對于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幾乎是決定性的。以上的這些維度的比較,并不是要說明電力體制改革是沒有必要的,而是說我們要客觀看待它的難度,增強對于改革進程與可能反復的耐心與韌性。對于我國而言,徹底透明化、改革現(xiàn)在的5級特權自由量裁調(diào)度體系,是解套電力部門幾乎所有問題的“鑰匙”。這恰恰是過去所有的政府文件與改革方向都未曾涉及的方面。
十四五電力規(guī)劃,需要首先是一個電力改革規(guī)劃,明確改革的總體目標(經(jīng)濟效率)以及操作性目標(特別是調(diào)度明確的價值觀與衡量標準、系統(tǒng)透明度、輸配體系產(chǎn)業(yè)組織等)、時間表、路線圖與組織體系。
種種跡象表明:我們的決策者對此是有清醒認識的。我們對電力體制改革始終抱有積極的期待與堅定的信心。